全国土地财政格局迎来了一个大转折。2022年上半年,全国国有土地出让收入2.3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大幅度下降31%。要判断其原因和未来趋势,需要对土地财政的来龙去脉做一个清晰的梳理。
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土地不是商品,需要的建设用地由政府从农民手里征用,并进行无偿划拨。
上世纪80年代,少数城市开始尝试土地有偿出让和住房商品化改革,1990和1992年国务院分别发布了土地出让的暂行条例和暂行管理办法,1993—1994年开始推行住房商品化改革,土地和住房才开始成为商品。
但土地交易从一开始并没有按市场原则来设计。地源仍来自政府征收农民的土地,只给很少的补偿(起初按被征土地农作物年产值的三到六倍计算补偿,后有增加,但多数情况下仍然严重违背等价交换原则)。
政府征收的土地进行初步开发后、通过协议方式(后房地产和商业服务业用地改为“招拍挂”方式)有偿出让,地方政府是唯一的建设用地垄断供应者。扣除征地补偿和拆迁费用后的土地收入、全部归政府所有。
按照早期的设计,住房改革实行双轨并行的体制,为中低收入居民提供保障性住房,为高收入居民提供商品住房。但在实行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利益导向使商品房比重越来越大,保障性住房受到挤压。2000年以后,商品房用地的收入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从此开始了土地财政时期。
土地财政体制的形成有某种必然性。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资源集中控制在政府手中,企业没有活力,居民收入被压低且增长缓慢。改革之初,为改变这种僵死局面,政府实行了大规模的放权让利和其他市场化改革。此后,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迅速增长,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增长加速、而全口径政府收入(起初包括财政预算收入和政府预算外资金收入,后加入土地出让收入和社保基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40.2%直线下降到1995年的15.9%(据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数据计算)。
在经济逐步走向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政府财政困难。为缓解政府财政资金不足,土地出让收入自然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一个补充来源。
所罗门的魔瓶一旦打开,就很难让其回到瓶子里了。伴随城市化快速发展,土地收入越来越大,成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1998年,全国国有土地出让成交价款约500亿元,相当于当年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10%。此后土地出让收入以不可抑制的高速度膨胀——2001年1300亿元,接近地方财政收入的17%;2011年3.3万亿元,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63%;2021年8.7万亿元,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78%(均不包括在地方财政预算内)。
从2001到2021这20年,现价GDP年均增长12.4%,现价全国财政预算收入年均增长13.4%,而土地出让收入年均增长23.4%,远超过了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计算)。
计算平均地价,2001年每公顷土地出让收入143万元,2011年为978万元,2021年为2393万元。20年间地价上涨15.7倍。
同期消费价格指数(CPI)只上涨58%,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只上涨38%(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计算)。
过高的地价大幅度推高了房价,并改变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由于不包括地价和房价,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已不足以反映真实的通货膨胀率。
而地价和房价飞速上涨,是几方面影响因素合成的结果。
从供给侧来说,一个正常因素是城市规模经济的溢出效应带来的城市用地和城市周边待开发土地升值。
从需求侧而言,城市化快速发展造成的房地产需求上升,而土地资源相对有限,持续拉动了房价和地价上涨。
第三个因素的作用可能更加突出,即长期以来货币增长大幅度快于经济增长,货币超发造成的多余购买力大量流向房地产,造成越买越涨、越涨越买的趋势,成了长期不破的资产泡沫。
第四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地方政府的作用。对地方政府来说,土地出让收入来得容易,用得方便,监管不严,透明度低,一方面可以用来搞各种地方政府想搞但没有其他资金来源的投资项目,既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建设,也包括政府楼堂馆所等各种自我服务设施,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包括“三公消费”在内的党政机关行政管理费用。
更严重的是,在政府垄断地源的情况下,大量的官商勾结腐败案件都与土地和房地产交易有关,给腐败官员带来了巨额收入,造就了一大批隐性富豪——在种种利益驱动之下,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其独占地位,通过控制土地投放量,借“招拍挂”尽量抬高地价,以获得最大收益。
这也导致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所占份额不断扩大,挤压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份额,形成与改革开放前面20年的放权让利截然相反的趋势。
于地价房价不断上涨,土地似乎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土地财政的基础条件是城市化带来的效率提高,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随着土地资源商品化、资本化,成为巨大的财富源泉,政府的土地收入也确实在过去的经济建设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推动了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条件快速发展完善,过去20年间对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作用不可忽视。
2001年,全国房地产企业的商品住宅平均售价2017元/平米,2021年升至10396元/平米,已是原来的5倍以上。但这远远没有反映出大城市房价的涨幅。在一线城市,房价涨了几十倍。而此期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名义涨幅不到6倍。
北京市四环路到五环路间的房价目前大约在5—10万元/平米,2020年北京市私营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9.06万元,只够负担1—2平米的房价。
目前大城市有房居民和无房居民的生活冰火两重天,天价住房让外来年轻人望而却步或最终不得不离开。留不住年轻人的城市,未来可能是人口老化、人力资源枯竭的城市。
其二,农民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宪法规定农村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因此农民在符合国家的土地规划用途的条件下、应当有处置属于自己的土地和获得合法收入的权利。城市周边土地大幅度增值,是城市规模经济的溢出效应所致,不应全归农民集体或个人,政府有理由通过税收提取土地增值的一个合理部分用于公共目的。
但在现行制度下,如政府以获利为目的,用征地的方式把土地收归国有,独占土地收入,实际是违反宪法的。目前,除一些大城市周边征地有高额补偿,在很多情况下农民并未获得足够的补偿。这对农村发展和提高农民的财产收入有严重的不利影响。
伴随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迅速提高,中等收入阶层不断扩大,90年代的住房改革又把原来的公有住房以低价卖给城镇职工,使他们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房产。这些本来创造了一个改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良好条件。
但过去20年,地价房价的过度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打断了这一进程,实际上形成了对新一代中低收入群体的掠夺。中年以下的中等收入人群或者背上了沉重的房债,或者成为永久的无房户。房贷和房租大大压缩了他们的消费能力,使他们很多人只在名义上属于中等收入阶层,实际生活水平无法提高甚至下降。
过高的地价和房价还推高了商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租金水平,把成本转嫁给各行各业和消费者,而占人口少数、囤有多套住房的富裕阶层,则可以轻松凭借房价上涨使财富快速升值。因此土地财政实际造成了财富的逆向再分配,是导致财富占有差距持续扩大和国民经济各行业间苦乐不均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全口径政府收入(包括财政预算收入、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全口径政府支出已分别上升到GDP的35%左右和40%左右,政府配置资源的程度大体回到了改革前的水平,其中土地出让收入扮演了重要角色。
市场配置资源的比重与上世纪80—90年代相比、被大大压缩,出现了背离改革大方向的趋势。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政府收入占比高的情况差异很大,后者占比高是因为政府承担了大量公共服务和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而我国这样高的占比中很大部分是政府直接参与资源配置。
其四,地价房价持续上涨和相关的金融扩张导致了越来越大的金融风险。2020年,房地产业创造增加值7.3万亿元,占GDP的7%,但房地产相关贷款已超过67万亿元,占银行贷款总额的39%,相当于GDP的66%。2020年我国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经高达80.7%,居民的房贷规模也越来越大(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和郭树清:“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2020年12月)。
地方政府的高负债也与土地有密切关联。这样高额的负债还不仅仅是因为地价和房价越来越高,也是因为融资的放大效应。
因为地价不断上涨,变相鼓励了房地产企业用外部融资囤地囤房,地方政府还可以用升值后的土地做抵押,借更多的贷款进行新的土地开发和其他投资。
资产泡沫和金融泡沫促使经济继续脱实向虚,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挤压作用,并形成了巨大的风险。 这些越滚越大的债务虽然有价格不断上涨的土地和房屋为抵押,表面上安全,但一旦地价房价由涨转跌,就可能引发坏债连锁反应,引爆金融危机。
综上所述,土地财政已经成为一个加剧经济结构失衡和财富分配失衡的因素,土地相关制度亟待改革。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今年的土地收入大幅下跌说明,现有的土地财政格局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1990年到2021年,全国已累计销售新建商品住宅202亿平米。房地产企业目前正在施工的房屋面积还有97亿多平米,此外,在住房商品化之前和来自非商品房的城镇居民住宅存量估计90—100亿平米。待目前施工中的住宅完工后,全国城镇住宅城镇居民住宅存量总共将达到380—390亿平米。
假设今后到2035年,城镇化率再提高10个百分点,达到75%,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从目前的42平米提高到50平米,城镇充其量还需要新建150亿平米住宅。未来14年,平均每年只需新建10.7亿平米住宅,城镇住房就将完全饱和。
而过去3年,平均每年新开工住宅面积高达15.9亿平米。这意味着今后房地产业哪怕只保持现有建设规模不再增长,未来也将出现非常严重的住房过剩,每年都会有约1/3的新建住房(5亿平米)卖不出去。相应地,房地产业对土地的需求量也将至少下降1/3(实际下降幅度可能更大,因为房地产企业目前还囤有相当数量的待开发土地),使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大幅度缩水。
据这些情况判断,今年上半年出现的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度下降,并非短期波动,很可能代表了土地和房地产市场走势的根本拐点。只是由于今年经济形势不佳,土地需求颓势更加突出。
在住房和土地需求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未来经济会发生什么?
大致会有硬着陆和软着陆两种可能。这里先对硬着陆的情况做一些大胆推测。作者希望这只是杞人忧天,推测错误。
土地成交可能转向量价齐跌。地方政府收入大幅度减少,以前那种不计成本、不算回报、寅吃卯粮、大拆大建、为了一时的政绩大手笔投资的格局难以为继,政府消费靠土地收入挥霍、钱权交易靠土地收入大行其道的局面也无法维持。靠政府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再是一个现实选择。
地价下降到一定程度,大量以土地为抵押的政府贷款将会成为不良贷款。银行的坏账率会大幅上升。政府债券到期不能兑现的情况可能大量发生。出现较普遍的偿债危机。
土地收入下降的直接原因是房地产业已进入衰退。今年上半年,房地产业的土地购置面积和土地成交价款分别下降了48%和46%。同期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下降27%和32%,意味着房价和销量同步进入下降期。地价下降还有一定的滞后期,但估计坚持不下去。房屋销售和房价大幅下降将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会有相当多的房地产公司倒闭,坏债大量发生。
房价降到一定程度,一些贷款买房的居民会发现与其继续还贷,还不如直接违约,因为市场上的现房可能变得更便宜。这与当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情况相仿,会使银行的处境雪上加霜,坏账进一步增加。政府可以禁止房地产公司降价售房,但房子卖不出去,房地产企业倒闭可能更多,对银行的打击可能更大。
大银行有政府支持,不会倒闭,但坏债会严重影响资金周转,把影响扩散到实体经济。中小银行将面临严重挑战,对实体经济影响可能更大,可能拖累整体经济进入较长时期的衰退。
有些人也许会主张重走大规模货币放水的老路来救经济、拉增长,但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最终需求在消费者一端,没有最终需求回升,大量增加流动性、只会加剧坏债螺旋形攀升。
但一旦发生上述情况,需要有理性的宏观政策应对,同时痛下决心,推进改革。如果应对得当,有可能使硬着陆变成软着陆,可以考虑以下措施。
如果发生全面的资金周转困难,货币当局可能需要释放一定量的货币维持资金周转,同时面对企业面临的困难,货币当局可以考虑降息作为一个选项来缓解企业的负担,但同时必须坚持货币总量控制,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利率与货币量的变化之间未必是线性负相关关系,不同政策工具的效果可能有很大差异,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财政政策不宜把重点放在扩大政府投资。保护失业者、低收入者和稳住最终需求是当务之急。强化失业保障,对未被失业保险覆盖的失业者(包括符合常住人口标准的失业外来农民工)进行普遍救济,促进消费需求尽快回升,引领经济回升。
政府收购适用的滞销房产,转为廉租房和公租房,并通过政府采购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一方面减轻房地产业和银行业受到的冲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把保障性住房覆盖面扩大到合理水平,分步使保障性住房能够满足城镇低收入和中下收入居民的居住需要,应覆盖未取得户籍的城镇常住人口。但整个过程必须公开透明、建立规范,防止幕后交易、私相授受。
改革土地制度,政府征地仅限于公益性和必须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参照市场地价予以补偿。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的商业性土地需求通过市场满足,不必通过政府征地。允许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允许农户闲置宅基地在不违反土地规划用途的条件下进行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取消对需求方身份的限制。
改革土地增值税制度,政府对土地交易中的大幅度增值部分征收适当比例的土地增值税,用于补充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足。
政府要过紧日子,压缩不必要和不急需的政府支出,转向量入为出的理财观念,把更多的资源留给市场配置,尽量减轻企业负担,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政府退出竞争性市场活动,转向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中心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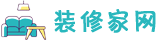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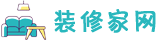
 友情链接
友情链接